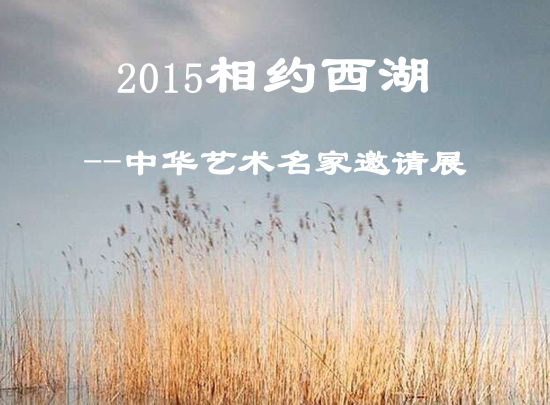当前位置: 首页 >
将军路上不追兔但可小憩 李才根
2012年06月06日 23:49:16 作者:N/A
台湾抽象绘画画家陈正雄讲,他的老师曾经说过,画家不是短程的冲刺,而是像万里赛跑,要跑几十年才能看出成果。实际上,讲出这个道理的中国大陆的老先生更多。
在中国画笔墨领域运动,不管是传统为学方法的 "金字塔" 模式,还是 "先求异,再求好"的现在 "摩天楼"模式,都是不可急迫的。而如法国一个名为杜尚的人,醍醐贯顶般的将笔一扔而成为 "大禅师" 的好事,你我最好不要去企及。
从表面上看,我做中国画有些杂七杂八,很不定性,有些像墨西哥的跳豆或在树枝间不停跳动的猴子。实际上,还在上研究生主攻花鸟时,那长安少陵塬下兴国寺老美院一间蓬户中心的 25W 灯泡下,我就经常翻着一部新版的山水画史和其他山水画册了。毕业后第一次99999见贾又福先生,他一句 "先临三年" 的话也着实让我从宋、元、明、清的代表性经典作品中有计划的选出了四十余幅,全部按原寸临作。后来这些临习和部分写生的作品除了得到赵步唐先生的指点外,还带到北京请张仃、常任侠、侯一民、王琦、钱绍武、贾又福的诸多先生批评。与此同时,一套台湾版的世界名画家全集购置在书案上,少不了去系统的翻阅。在我将研究的方向锁定在西部山水的理论研究和作品创作上后,数次子带车,过祁连、穿天山、走昆仑、越界山,上下阿尔金山、横短山、唐古拉山、岗底斯山... ... 。这几年专题做下来,加上三十年西部生活的积累,对西部山水把握算是 “心中有数”了。
现今做中国画,难处不在“中国画自身规律”的制衡,也不在于突围“法久弊深”块垒的艰辛,而是工业化时代的快捷生产方式和信息时代的纷扰。时代的快捷就是没完没了地朝前赶,更意味着“套路制造”,很容易不断的重复自己和别人。信息时代在带来各种机遇的同时又造就了批量的信息傻瓜,在信息超市中由于很难做到“信息节食”和选择土的不确定而死在无力消化上。
就说绘画是一个过程。在路上,难免会开小差和有一些应付。开小差是一种调节,应付是一种能力。因此,我的作品具有较明显的时段性和闪烁性,就如这个册子中以花鸟为主的作品,一做完,“好得不好的都是我的”。接下来就是继续前进了。
说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,过红海,来到旷野地玛拉,三天没找到水喝了,好不容易找到的又是苦水,其境遇可想而知。实际上,泉水和棕树就在不远的以琳。这是一篇短文中讲《圣经.出埃及记》说到的事。很明显,过了“玛拉”,“以琳”就不远了。
我也这样想。
出版物图片如下:(书中共包含了画家李才根花鸟、山水创作作品33幅)
封面A


封面B


画家李才根近影